手机版 欢迎访问ysw28自媒体运营网(www.ysw28.com)网站
第100位主持人 | 潘文杰
今年,电影《她消失了》为我们展现了一场东南亚的“怪胎秀”。在这部都市传说中,一对夫妻在东南亚旅行,妻子在试衣间试衣服时突然失踪,丈夫寻找多年,终于发现妻子已在舞台上变成了“人猪”。这样的电影内容,加上今年泰国男模餐厅“被咬肾”的传闻,吓坏了一些想去东南亚旅游的游客。虽然泰国政府已经辟谣“被咬肾”的传闻,但类似的故事还是让人难以忘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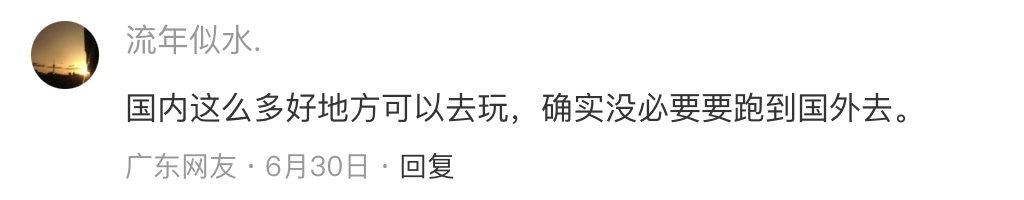
另一部商业片《All or Nothing》是一部反诈骗教育片。在这部电影中,失意的程序员和渴望出名的模特被高薪的海外招聘所吸引,决定出门闯荡,却意外卷入一场精心策划的网络骗局。这部电影反映的是“缅北骗局”。8月,缅甸商务部长昂乃乌就缅北网络诈骗问题作出回应。他表示,缅北网络诈骗问题并没有媒体报道的那么严重,国际舆论中有很多虚假新闻,只有来到缅甸才能了解真相。与此同时,关于缅北的新闻和传说仍然铺天盖地,真假难辨。
未来,类似的电影或许还会有更多。电影《鹦鹉杀人》定档9月15日上映,被誉为“首部讲述杀猪诈骗案女性的电影”。据悉,该片故事取材于大量“杀猪诈骗”真实案例,真实再现了“以爱之名杀猪”的犯罪套路。电影的口号是“你在恋爱,他在出轨”。这看似是一部诈骗教育的公益片,实则却是一部需要观众为票房做贡献的商业电影。
如果我们可以将这类电影称为“恐怖电影”,那么为什么它们如今如此受欢迎?
01 恐惧文化盛行,反映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
林子仁:其实我没看过《消失的爱人》和《All or Nothing》,但我觉得只要在社交网络上浏览别人的帖子,就能理解这两部热门国产电影的剧情。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两部热门国产电影的话题导向性很强。我记得《消失的爱人》的宣传提到灵感来自泰国妻子坠崖事件,而《All or Nothing》则与近期密集报道的缅甸诈骗犯罪新闻息息相关。话题导向性先行的结果是观众很容易混淆艺术创作与社会现实的界限,把电影当成一部剧情更精致、戏剧冲突更多的纪录片来看,从而会引发“国内有那么多好去处,真没必要出国”的观影感受。
恐惧似乎已成为一种集体情绪,但这一现象并不局限于中国。早在1997年,英国社会学家弗兰克·弗雷迪就提出了“恐惧文化”的概念。他认为,“恐惧对人们思考生活方式和应对不确定性的方式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公众言论不断引用恐惧话语,甚至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也越来越带有煽情色彩。”导致西方出现这一现象的因素有几个,其中之一是人们对伤害和风险规避越来越敏感,被定义为有风险的生活经历范围也不断扩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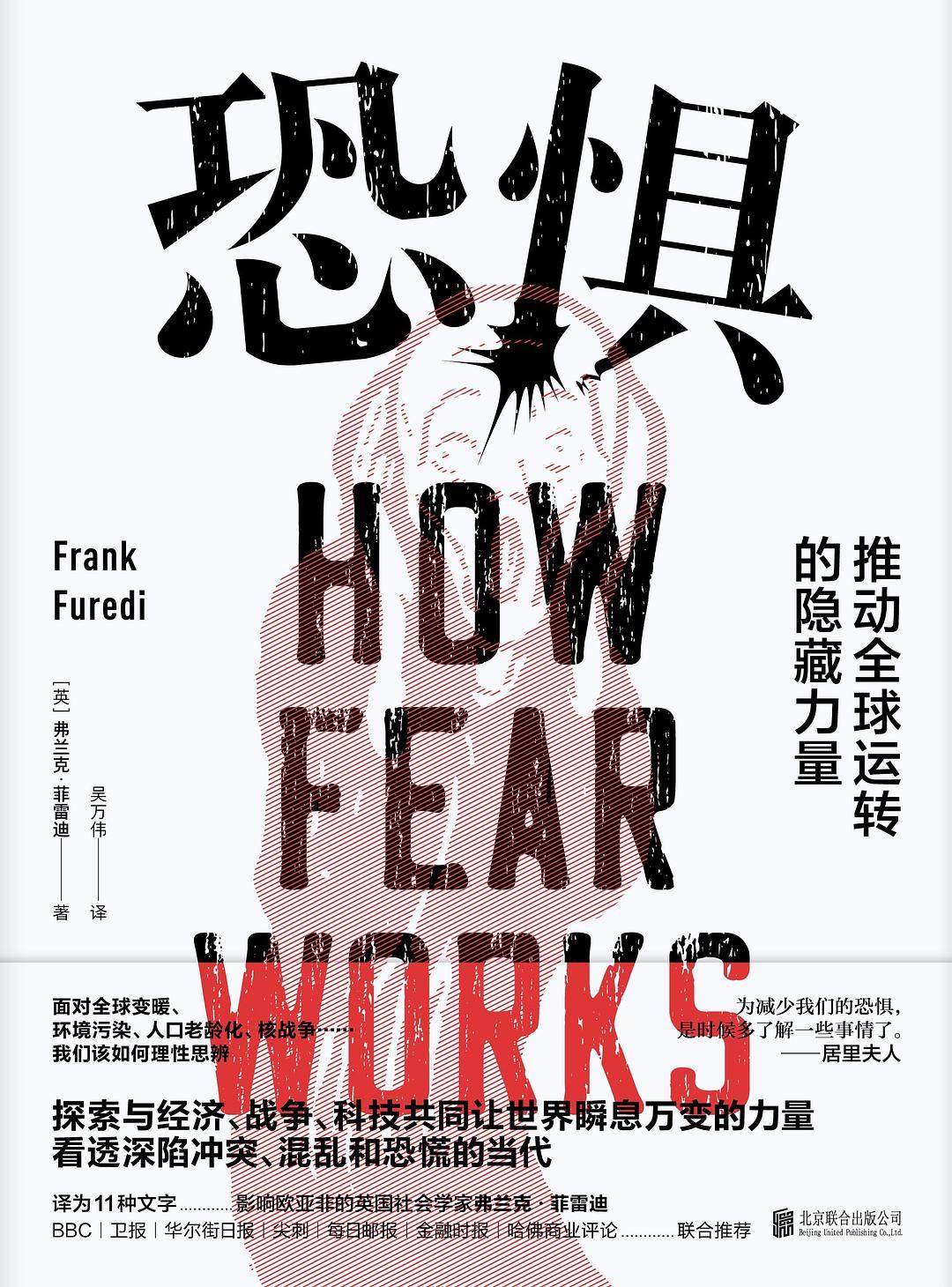
菲雷迪提到的另一个因素,也是和我们谈论的“恐怖电影”更相关的因素,是大众媒体在塑造恐惧文化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与其说媒体创造了恐惧,不如说它为人们间接体验恐惧提供了一种媒介。”菲雷迪在《恐惧》一书中引用了法理学家克里斯托弗·古泽利安的观点,指出恐惧的间接性是当代恐惧文化最明显的特征。“今天,恐惧大多是由风险的传播所创造的,而不是个人的亲身经历。”
归根结底,恐惧文化之所以盛行,是因为道德困惑、缺乏信任,更重要的是对未来不确定性的焦虑。人们现在倾向于从消极的角度看待不确定性,因此变化本身就具有威胁性和令人恐惧性。这种变化可能是在国外,也可能是某种系统性变化。
许璐晴:这件事情让我感触颇深。我已经很久没用安卓手机了,有一次回家用我妈的手机,打开手机上的浏览器,看到首页上有很多煽情、恐吓的新闻,大多还配上几张电影截图,充满了稀奇古怪甚至色情的新闻,比如女大学生在东南亚失联最后在红灯区被找到、女大学生失踪后入山沦为性奴、女大学生在酒吧喝醉被人捡到身亡等等。这些信息很大程度上建构了她对外部世界的想象。
潘文杰:用恐惧、威胁作为卖点,记者多多少少都能理解。在KPI的引导下,作为内容生产者,我也会思考什么样的内容更吸引人。带有悬念、刺激、威胁等的标题自然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流量高也是很正常的。尤其在自媒体时代,大家都在争夺注意力,内容工作者追求这些也是必然的。
恐吓本身还能带来安全感——啊,因为他们这样做了(比如去了缅北或者泰国)才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就不用做了,甚至还能带来优越感——连中国科技大学的博士都被骗了,而我没有。
02 只要你保持冷静,就不会有危险。保守的“岛屿宇宙”只会缩小。
董子琪:我想到了栾宝群讲的那些奇葩小说——鬼伪装成人在集市卖鸭子,所谓的鬼就是人群中的陌生人。所以无论是缅北诈骗案,还是家暴男子,都像是“鬼”的化身。有一段时间,我痴迷地看《今日说法》系列。其中有一个案例就是网络交友诈骗。真相曝光后,警方经常提醒广大男性用户,不要被“女鬼”欺骗。那些声音甜美、面容姣好的女性,并不是真心想跟你约会,而是像画皮一样的“女鬼”冒充你骗钱、夺你性命。这类案例看多了,会有点心惊胆战。这么多年过去了,“红脸骷髅”这个比喻,依然在世人间流行。
这些智慧和启迪的话语让我想起了中国传统的“以神道教化”,即儒家知识分子不相信鬼神报应之说,但为了警示世人,规范自己的行为,也运用了鬼神之说。比如祥林嫂听说再婚的女人死后会被撕成两半,对“十八层地狱”的信仰,就是这样的产物。祥林嫂真的害怕人死后有灵魂,因为吕四先生和很多权威告诉她,这个世界没有错,要至死守贞。至于她的焦虑和恐惧,得不到救赎,那是最微不足道的。
“他们在意的是人心的稳定和社会秩序的维护,也就是希望让坏人感到恐惧,消灭邪恶,但根本不在乎在这人世间痛苦中受苦受难的人们的灵魂的救赎。”日本学者丸尾常吉的这句话,或许也可以用来评价恐怖电影。
这些恐怖片和真正的恐怖片有什么区别?《消失的爱人》和《孤注一掷》不是都假设了这个世界的稳定和外面世界的动荡吗?真正的恐怖片,即便有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的区分——比如《迷雾》和《寂静之地》——也会假设恐怖会一点一点蔓延,没有所谓的安全之地,最终所有人都会被卷入其中。换句话说,在恐怖片里,人们只要保持安静就不会有危险;而在恐怖片里,魔鬼、僵尸、怪兽迟早都会找上门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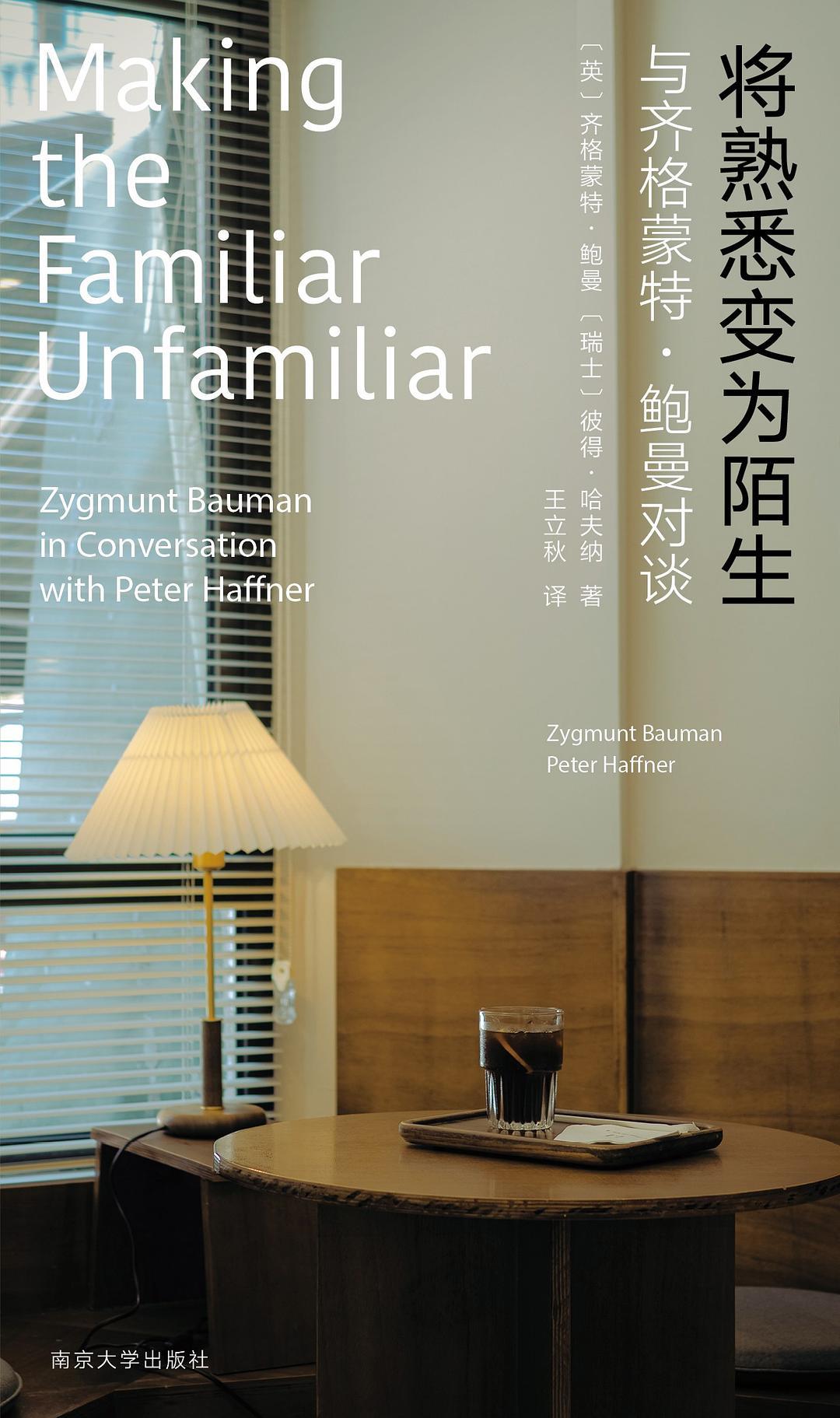
鲍曼在对话录《把熟悉变成陌生》中重申了弗洛伊德的结论:现代人之所以产生精神痛苦,是因为为了文明提供的安全而牺牲了太多的自由。他认为,恰恰相反,人们为了自由而牺牲了太多的安全。不管鲍曼说的是否正确,但这是否是许多人感到恐惧的真正原因呢?
尹庆禄:利用民众的恐惧心理来排斥异己,划分“安全岸”与“危险岸”,也是近年来日本电影/动画谱系中常见的做法。不同的是,正如社会学家吉田俊也在其著作《平成时代》中指出的那样,对崩溃的恐惧和担忧并非来自某种外部打击,而是从内部产生的——吉田将平成时代定义为“失败的时代”。日本在全球化、信息化、少子老龄化等潮流中遭遇挫折,失败的预感早已在上世纪 90 年代的《阿基拉》、《新世纪福音战士》、《20 世纪少年》等作品中有所体现。这些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那就是对世界末日来临的恐惧。

评论家宇野恒弘认为,随着日本新自由主义的崩塌愈发明显,千禧年后的日本文艺作品进入了“大逃杀”和“决胜”的模式。无论是校园生存电影《大逃杀》,还是动画《死亡笔记》,都以世界的不透明/无序为前提,不假思索地迈出步伐,传递出如果待在家里就会被杀,所以要靠自己活下去的信息。这形成了排他性的“岛宇宙”社会,区分敌人和朋友变得重要。
这类作品保守孤僻,其所挖掘的情感与《消失的爱人》和《孤注一掷》如出一辙。当然也有不同。比如日本大逃杀作品的舞台多设在日本,其崩塌也是内部的,而这些国产中国电影则区分了“安全的国内”和“危险的国外”。但我觉得情感的延展性很强,上一秒还在担心东南亚,下一秒可能就担心邻居了。保守的“岛国宇宙”无法主动扩张,只会萎缩。

03 能拍出好写实的人,肯定是果断性不够
潘文杰:我们想要相信的现实和真正的现实之间是有差距的。美国《科学》杂志曾刊登麻省理工学院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显示,在社交媒体上,假新闻的传播速度比真新闻快6倍,而且假新闻被转发的几率更大。研究人员称,公众更愿意分享假新闻,因为它更具有煽动性。在读者眼中,这些假新闻比真相更“真实”,更像现实。那么,所谓恐怖电影中的现实主义和过去的现实主义有什么区别吗?
许璐晴:最近有评论说,今年暑期档的大热电影充斥着“塑料现实主义”,看似在揭露社会黑暗,实则是为了抓住热点的“问题电影”。现实主义和伪现实主义到底有什么区别?我最近正好在看纪录片《梦想背后》,讲的是娄烨导演的《风中一朵雨做的云》的制作过程。我觉得拍好现实主义的人,一定是不够果断,对什么是“正确”没有清醒的认识。
直接呈现、直接判断话题,当然比呈现一个复杂、模糊、微妙的现实要简单得多,也更令人愉悦。其实,不只是电影人,在书籍领域也是如此,现在很多文学书籍的营销都是“社科化”的,只需要把复杂的文字精简成简单的宣言就行了。一位编辑跟我聊起这件事,说或许这样会给人更大的“收获”感——看完这本书,至少能收获一个道理,明白些什么。谁有时间花在一些复杂而无用的感情上呢?
评论者也容易被话题带入,因为这是最省力的制作方式,更能满足读者的期待。面对直觉型的创作者,我经常不知所措,该怎么写他们的采访?他们似乎更在乎矛盾和细节,思路总是跳跃纠结,或者说,他们没有想那么多。但受访者不善于总结和判断,所以写出来的对话不够好,似乎没有切中要害。我很喜欢电影《野蛮入侵》,暑期档表现平平,宣传为了赢得更多票房,会挑出符合女权主义标准的台词,强调故事展现了母性的困境,但电影文本的复杂性远超这些话题拼盘。相反,“塑料现实主义”很容易被话题概括。 它们利用人们对话题的想象来构建框架,文字只负责乖乖地填充骨架,让它们看上去更加天衣无缝,而不是造成任何的撼动。
尹庆禄:“恐吓”和“恐怖”的区别很有意思。恐怖带来的是内心的动荡和焦虑,这可以成为构建新自我的机会;而恐吓带来的是“安全而刺激的感觉”。只要你能识别出“他者”,也就是杀猪骗子,站在“自己人”那边,你就是安全的。我觉得这也是现实主义和伪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
吉田俊也举了一个例子:1995年日本沙林毒气事件后,媒体制作了一系列奥姆真理教报道节目,人们像看都市传奇电视剧一样痴迷地观看,感到害怕的同时又享受其中的内容。吉田认为,这种方式让人们把信徒当成他者来解释他们为何与日本社会格格不入,但这样一来,也剥夺了人们从根本上质疑现实的可能性。同样,《All or Nothing》等“TikTok类电影”也带有这种都市传奇的廉价情绪。我自己也喜欢看《神说了算》《朋友游戏》等日本校园逃亡漫画,它们确实给人带来强烈的快感,但快感过后,便是无尽的虚无。
Copyright © 2002-2024 www.ysw28.com 版权所有 非商用版本